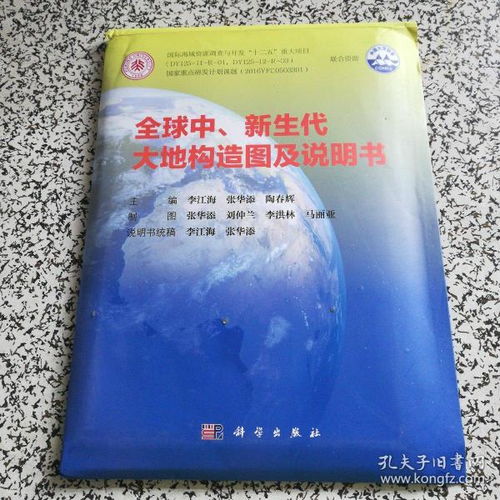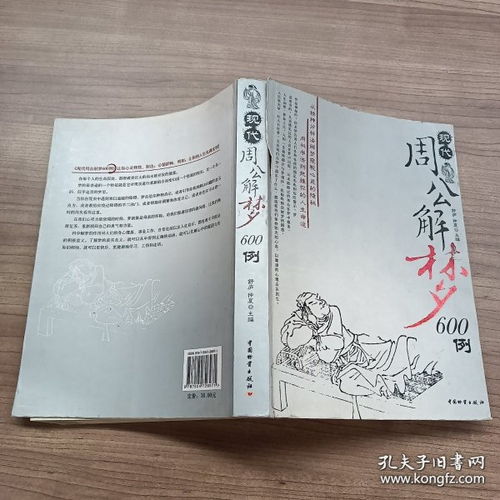在中國古代文化中,貓始終占據著一席風雅之位。南宋詩人陸游曾以“裹鹽迎得小貍奴”描繪迎貓入戶的儀式感,又以“盡護山房萬卷書”道出貓咪守護書齋的文人雅趣。這般詩意的描摹,正是貓咪與風雅之事交織的絕佳寫照。
古人迎貓講究儀軌,據《禮記》載“迎貓為其食田鼠也”,而文人雅士更將此事詩化。陸游詩中的“裹鹽”源自民間習俗——以鹽為聘禮,鄭重其事地迎請貓咪歸家。這般儀式,既是對生靈的尊重,亦是對雅致生活的追求。當小貍奴踱步于青磚黛瓦間,俯仰于翰墨縹緗側,便為書齋平添了三分靈動七分禪意。
貓咪護書之說,實則兼具實用與象征。古籍易遭鼠嚙,貍奴捕鼠天性恰成天然守護。然更深層處,貓咪臥守書卷的姿態,暗合文人“鬧中取靜”的處世哲學。明代文震亨在《長物志》中特設“貓窩”條目,主張“設貓窩于書房左近”,正是將貓咪納入書齋雅器體系。那蜷縮于硯臺旁的毛團,仿佛在提醒世人:真正的風雅,在于與萬物共生的從容。
歷代文人多與貓結緣。黃庭堅曾嘆“秋來鼠輩欺貓死”,白居易亦寫“貍奴護我寒窗下”,至清代《貓苑》更集錄百則貓事。這些文字中的貓咪,時而是夜讀時的溫暖陪伴,時而是茶煙裊裊間的靜觀者,甚至成為畫家筆下的水墨主角——沈周《貍奴圖》中那回眸的靈貓,與案頭瓶梅相映成趣。
當今時人養貓,雖少裹鹽舊俗,卻延續著與貓共處的風雅。在窗明幾凈的居室內,觀貓嬉戲于書架之間,聽其呼嚕伴翻書之聲,何嘗不是現代版的“山房護書”?當我們為貓咪置備雅致的食器、編織精巧的窩墊,其實仍在踐行著古人“格物致知”的生活美學。
小貍奴從古至今躍然于文人筆端,不僅因它捕鼠護書的實用,更因它身上那份不受拘束的靈性。正如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所言“貓的世界沒有世俗”,這種超然物外的氣質,恰是風雅精神的本質——在凡常生活中,守護一方精神的山水。當我們在鍵盤上敲打文字時,若有貓咪慵懶地臥于一旁,便是接續了千年未斷的風雅弦歌。